引言
朱熹在《中庸章句序》中曰:“《中庸》何为而作也?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。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,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。其见于经,则‘允执厥中’者,尧之所以授舜也;‘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’者,舜之所以授禹也。……自是以来,圣圣相承:……惟颜氏、曾氏之传得其宗。及曾氏之再传,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,……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。” [1]在此,朱熹提出了两个关键论点:其一、他不仅把“执中”与“中庸”联系在一起,作为儒家道统传授的核心内容,而且源头追溯至“上古圣神”(伏羲等圣人)。[2]朱熹此论并非完全没有文献依据。因为尧、舜、禹三人之间以“允执厥中”传授,在《论语》中是有明确记载的。而“人心,道心”虽出自“伪古文尚书”,《荀子》确有相近的记载。但这并不意味着《中庸》的思想一定是《大禹谟》的延续。因为从《大禹谟》的字面上看,“允执”的对象完全可以理解为“惟精惟一”,所以“中”并不一定就是“中道”。同时,上述文献并未说“中道”思想始自伏羲。其二、他论述了伏羲为首,中经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的道统谱系。[3]孔子至孟子的谱系韩愈虽已提出,但并没有作出有力的说明。由此,有待于解决两个问题:其一、朱熹把《中庸》与《尚书》联系到一起,并把“中庸”思想源头上溯至伏羲,其理由是什么?这是朱熹的首创还是前人之功?其二、朱熹肯定“孔、曾、思、孟”之传承谱系的理由是什么?以下,本文将尝试论之。
一、“中庸”成为儒家道统核心思想之滥觞
“道统”一词虽唐代才出现,但儒家的“道统”思想其实可追溯至《中庸》。该书言:“仲尼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。”[4]如此,便建构了从尧、舜至孔子的传统谱系。但把伏羲等上古圣人、子思、孟子及其思想纳入其中,不仅是较晚的事情,而且经历了一个形成、确立的过程。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?须从《尚书》谈起。从现有可信的文本看,“允执厥中”一语既见于《论语》,又见于《尚书》,而《尚书》比《论语》早得多,所以宋人(如朱熹)在追溯思想根源的时候,定会挖掘至更早的文献。现版《尚书》据传是汉代孔安国所注,不过他在释“允执厥中”时未释“中”,只释了“允”,而以“信”释“允”,这也只是常训。孔颖达则不仅解释了“允”,而且解释了“中”:“民心惟甚危险,道心惟甚幽微。危则难安,微则难明,汝当精心,惟当一意,信执其中正之道,乃得人安而道明耳。”[5]尽管“中正”与“中道”“中庸”不能完全等同,但意思接近。如此,就为把《尚书》与《中庸》统一起来开辟了道路。也可以说,孔颖达是这一思想的开创者。为何孔颖达会把“执中”解释为“执中正”呢?缘由在于“中”本身就有中间、中正的意思。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中,内也”,“中,正也”。[6]“内”指中央、中间,相对于外而言;“正”指不偏不倚、恰到好处,相对于偏而言。许慎的解释符合古人的观念,因为“尚中”观念早在商周时就有了。如《尚书簚酒诰》曰:“丕惟曰,尔克永观省,作稽中德。”《尚书簚吕刑》曰:“哀敬折狱,明启刑书,胥占,咸庶中正。”[7]又如《易经》强调“中行”,如《夬卦》九五有言:“苋陆夬夬,中行无咎。”[8]遵行中道便能获吉。后来的孔子正是在综合上述思想的基础上,提出了“中庸”概念。而后子思又加以继承,并以为《中庸》的核心概念。因此可以说,孔颖达以“中正”释“中”,就为《尚书》《中庸》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。
孔颖达更为重要的贡献,不只是提供了上述的可能性,而是以“中庸”为核心,统一了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三者的思想。孔安国解“皇建其有极”云:“大中之道,大立其有中。”尽管孔安国及其他汉人[9] 业已使用“大中”释“皇极”,但并没有统一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的意识。而孔颖达则实现了统一:“‘大中之道,大立其有中’,……凡行不迂僻则谓之‘中’,《中庸》所谓‘从容中道’,《论语》‘允执其中’,皆谓此也。……君以大中教民,民以大中向君,是民与君皆以大中之善。君有大中,民亦有大中,言从君化也。”[10]孔颖达不仅把三种文献作了统一,而且进一步强调了“中庸”的重要性:虽然《论语》有“执中”之说,《中庸》有“用中”之论,但并没有说社会和谐的关键之一在于“中庸之道”。这一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,比如对中唐的柳宗元、宋初的胡瑗等。
既然孔颖达统一了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,那么能否说在其看来,“执中”是圣人之间一脉相承的思想呢?遗憾的是,他并未明言。究其主要原因在于:其一、佛教法统思想虽已形成,但影响还不算大(下详);其二、尽管天台、禅宗、华严等宗派在隋朝就已诞生,但直至唐初,也都还处于形成、发展时期,影响远不及中唐,而且朝廷统一经学的做法本身就是振兴儒学的一个重要举措。所以,尽管孔颖达也反对佛教,然而他的做法只是不同意佛教的主张而已,并未加以严厉批判,尚未有建立儒家道统的迫切感。如他在《周易正义序》中说:“其(《周易》)江南义疏,十有余家,皆辞尚虚玄,义多浮诞。原夫易理难穷,虽复‘玄之又玄’,至于垂范作则,便是有而教有。若论住内住外之空,就能就所之说,斯乃义涉于释氏,非为教于孔门也。既背其本,又违于《注》。”不同意佛老的“空无”之说,成为他注《周易》的主旨,目的只是“考察其事,必以仲尼为宗”[11]。
到了中唐,汉传佛教义理愈发成熟,影响与日俱增,皇帝至平民愈益高度崇拜。韩愈之言“‘百姓何人,岂合更惜身命!’以故焚顶烧指,百十为群;解衣散钱,自朝至暮,转相仿效”[12]虽有夸张之处,但大体是事实。从上到下的宗教狂热,实是佛进儒衰的表现,故柳宗元的表亲吕温便有“儒风不振久”[13]的感叹,这也是韩愈大力辟佛的关键缘由。然作为韩之密友的柳宗元,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,可谓截然不同。尽管他也反感佛教出家、不事劳动等主张,不过在其看来,韩愈对佛教的理解是低层次的“忿其外而遗其中,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”,没有认识到佛教的优点,“凡为其道者,不爱官,不争能,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”,而这正是自己好佛的缘由,“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”。[14]
与韩愈一样,柳宗元受梁肃与禅僧“道统”的启发,[15]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观。但两人的具体主张大不相同。韩强调夷夏之辨和建构儒家道统谱系。他说:“凡吾所谓道德云者,合仁与义言之也,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,去仁与义言之也,一人之私言也。”[16]这一“义理”论述是其道统观的关键内容之一。柳则主要以“中道”来概括儒家思想,[17]并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圣贤相传的。他说:“圣人之为教,立中道以示于后。曰仁、曰义、曰礼、曰智、曰信,谓之五常,言可以常行者也。……是故圣人为大经,以存其直道,将以遗后世之君臣,必言其中正,而去其奇邪。”柳虽也讲“仁义”,但认为“中庸”更具有代表性和核心的地位。具体言之,“中庸”是圣人之教的代表,包含了“五常”,因而是“大经”,且是为人处世的法则。他进一步指出,这些都是尧舜等圣贤留传下来的:“吾之所云者,其道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高宗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皆由之。”“吾之所云”即是前文所言“夫刚柔无恒位,皆宜存乎中……应之咸宜,谓之时中”。甚至认为舍此便无圣人之道,“立大中,去大惑,舍是而曰圣人之道,吾未信也”。[18]这些观念可谓是柳宗元的最重要创造,亦可谓是以“中庸”作为儒家“道统”传承核心思想之滥觞。学界对柳宗元以“中庸”作为调和儒释之依据,曾有关注,“大中者、为子厚说教之关目语,儒释相通,斯为奥秘”,[19]遗憾的是未给予足够的重视。如此,自然不能明晰他对理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。[20]
或许有人会说,在学术史上,李翱率先抬出《中庸》批评佛教,且有“曾子之死也,曰:‘吾何求焉?吾得正而毙焉,斯已矣。’此正性命之言也。子思,仲尼之孙,得其祖之道,述《中庸》四十七篇,以传于孟轲”[21]之语,那为何不能说此是以“中庸”(或子思)为核心的儒家“道统”观之源头呢?笔者认为,尽管他以《中庸》批判佛教的做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然而在其看来,儒家思想的核心并非“中庸”,而是“诚”,且未以“中庸”为核心来构建道统谱系,所以,理学家以“中道”为核心建构出来的道统谱系应以柳宗元为开端。只不过,在谱系上,柳既未上溯至伏羲也未下延至思孟,而这一工作是由宋人逐渐完成的,其中孙复、胡瑗、二程和朱熹起了关键的作用。
二、“中庸”成为儒家道统核心思想之历程
在宋儒中,除了理学家外,重视“中庸”的士人很多,主要有宋初儒士孙复、胡瑗和佛教徒契嵩。
孙复是宋初三先生之一,亦是宋初批评佛教的代表性人物。他视韩愈为偶像,承继了韩的道统观。他指出,“吾之所谓道者,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道也,……韩愈之道也”,而“道”的内容在于“夫仁义礼乐,治世之本也”。在此基础上,孙复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观:“所谓夫子之道者,治天下,经国家,大中之道也。其道基于伏羲,渐于神农,著于黄帝、尧、舜,章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……噫,自夫子没,诸儒学其道、得其门而入者鲜矣,惟孟轲氏……韩愈氏而已。” [22]孙复把“中道”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,并上溯至“伏羲”下延至“韩愈”。这与韩愈有明显区别,而更接近柳宗元。[23]极有可能,他并未意识到“大中”之道与“仁义”之道的区别,致使两种明显不同的道统观在其思想中并存不悖。[24]然而,尽管孙复未对“大中”与“仁义”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,但把伏羲作为“中道”提出者的思想对后来的理学家有直接的影响。
同样作为三先生的胡瑗,却对“中庸”作了较为系统的发挥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“中庸”作为了自己经学思想的核心。[25]胡瑗不仅把“中庸”作为君子的内在品质和“复性”的方法,“君子之道,积于内则为中庸之德,施于外则为皇极之化”,“有大中之道,则所行无过与不及。如是,故能治心明性,以复于善道”,[26]而且作为治理天下的关键要素,“圣人之治天下,建立万事,当用大中之道”。这些思想柳宗元和孙复都是没有的。不过,他们也有相同的地方,即胡也认为“中庸”思想是圣人相传的:“大中之道行天下,无叛道之士,四海无违教之民,皆知礼义,皆为君子也……故尧、舜以此道而能为二帝;禹、汤以此道而能为三王;周公思兼三王,致成王于有道;孔子不得其位,则著之于《六经》。”“中道”既是圣王之所以成为圣王的依据,又是圣人传承的核心内容。既然是“依据”,那么“大中之道”的地位便远高于圣王,不仅百姓要遵循,圣人亦如是。胡瑗强调,君主必须率先遵守,如此百姓才能效仿:“言身能唱率大中之道,然后可以感天下之心,成皇极之风教也”,[27]“在上者当修治充广五常之道,使下之民睹而效之,故谓之教”。[28]胡瑗对“中庸”作了较详细的分析,并以之为核心构建圣人传承谱系。加之他在当时的巨大名望,还有程颐老师的身份,其上述主张自然对理学家以“中庸”为中心建构道统谱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孙复、胡瑗以“中庸”作为圣人传承法宝的做法直接影响了僧人契嵩。契嵩对“中庸”的重视,除受前辈智圆的影响外,主要源自以胡瑗、孙复等为代表的宋代新儒士的刺激。1059年,契嵩说:“若今儒者曰‘性命之说,吾《中庸》存焉’。”可见此时《中庸》已成为儒士回应佛教挑战的主要思想武器。所以,他作《中庸解》等论述中庸的文章,以与儒者争辩。这些文章,从表面上看,主旨在于强调儒之“中庸”与佛之“中道”相近,故有“以中庸几于吾道,故窃而言之”之语,其实调和仅是手段,力主佛高于儒才是目的。为此,他对儒家道统观的论述常常自相矛盾。一方面,他极力肯定圣人传承“中庸”道统,认为“中庸”与“仁义”相比,更能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,故曰:“至于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之世,亦皆以中道、皇极相慕而相承也。《中庸》曰:‘从容中道,圣人也。’孟子亦曰:‘中道而立,能者从之。’岂不然哉!如其不修诚,不中正,其人果仁义乎?”又曰:“夫中庸者,盖礼之极,而仁义之原也。”于是,他极力反对韩愈以“仁义”为核心的道统观,“未闻止传仁义而已”;另一方面,他认为舜、孔子、颜子、子思属于“能中庸者”,武王、周公属于“能以中庸孝者”,而对尧、禹、文王是否能“中庸”则表示怀疑,理由是“孔子不言,而吾岂敢议焉”,并且对“学于子思”的孟子能否“中庸”也表示怀疑。如此这般,契嵩巧妙地否认了儒家“中庸”道统的完整性、合理性。具言之,契嵩肯定以“中庸”为核心的道统观,目的在于调和儒释;而质疑、贬斥以“中庸”为核心的道统观,是为拔高佛而贬低儒。如,他在对“中庸”之“中”进行本体论阐释时,就强调诸子百家所谓“中”只是形下的,唯有佛家所谓“中”才是真正形上的“中”。他说:“夫事中者,百家者皆然,吾亦然矣;理中者,百家者虽预中而未始至中,唯吾圣人正其中以验其无不中也。曰心曰道名焉耳。”[29]佛家之“中”非一般方法意义的“事中”,乃是形而上的“心”或“道”,即为“理中”。
1062年,契嵩的《辅教编》《上仁宗皇帝万言书》等论著被放在枢密院与中书省展览71天,让大臣们观看。[30]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契嵩在士人中的影响力,其力主佛高于儒的立场更是刺激了士人,尤其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,促使后者加快了对“中庸”进行本体论诠释的步伐。
契嵩之后,司马光曾对“中庸”有较多阐述,甚至尝试过形上诠释,[31]但未涉及道统,故本文从略。从道统上阐释,并最终确定“中庸”为儒家道统核心的,无疑是二程及其后学。
在道统的建构上,首先,二程承继孙复,把“中庸”思想的源头追溯至伏羲。具体的论证方法是,二程一方面指出,了解“时中”是把握《中庸》基本精神的前提,“欲知《中庸》,无如权,须是时而为中”;另一方面又认为,古圣人伏羲、尧、舜恰是熟练运用“时中”的代表人物,“古之伏羲,岂不能垂衣裳,必待尧、舜然后垂衣裳?据如此事,只是一个圣人都做得了,然必须数世然后成,亦因时而已”。[32]依此,伏羲便成为利用“时中”(或“中庸”)的鼻祖。
其次,二程把儒家心性之学的源头直接追溯至伏羲。程颐说:“《孔序》:‘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《三坟》,言大道也;’……所谓大道,虽性与天道之说,固圣人所不可得而去也。”而“《中庸》乃孔门传授心法”,“《中庸》首先言本人之情性”,[33]如此便把儒家心性溯至“三皇”时期,不仅使儒家心性思想更源远流长,而且使《中庸》与古圣人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。
再次,从本体论的高度对“中”进行了论证。二程云:“中庸,天理也”,“中即道也”,“天理,中而已”。[34]天理具有绝对性、普遍性、永恒性,“中庸”亦然。“中”不再仅仅是一个形下的概念,在高度上完全可与契嵩所说佛教之真正的“中”平起平坐。如此,便可在本体论上回应佛教的挑战。
最后,以《中庸》为中心,确立了孔、曾、思、孟的传承谱系。二程说:“孔子没,曾子之道日益光大。孔子没,传孔子之道者,曾子而已。曾子传之子思,子思传之孟子,孟子死,不得其传,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。”[35]又说:“《中庸》之书,是孔门传授,成于子思,传于孟子。”[36]在此,二程就以《中庸》为中心,建构了孔、曾、思、孟的传承谱系,此后该谱系为理学家广为接受。如吕大临说:“《中庸》之书,……孔子传之曾子,曾子传之子思,子思述所授之言,以著于篇。”[37]
二程及其弟子的上述思想,为朱熹“《中庸》何为而作也?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。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,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”之论奠定了基础。接下来,需要解决的问题是:如何“做实”曾子与子思之间的传承关系,因为《论语》有孔子以“鲁”评价曾子之明确记载。
三、以“中庸”为核心思想的儒家道统谱系的最终确立
尽管儒家的“道统”谱系至晚可溯源至《中庸》,但唐宋儒士把子思、孟子等孔子之后的儒者纳入新谱系中,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。在原始佛教时期,佛教内部就开始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传承系统,即佛教的法统。汉传佛教法统的建构始于隋唐时期,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天台宗和禅宗的法统,至晚在韩愈、柳宗元时期,已经形成了天台“九祖”和禅宗中士“六祖”的法统。[38]韩愈受此影响,创造性地建构了以孔、曾、思、孟为传承,以尧舜为始祖的儒家道统谱系。他说:“‘斯吾所谓道也,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’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,文武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;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”又说:“孟轲师子思,子思之学盖出曾子,自孔子没,群弟子莫不有书,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。”[39]为避免道统中断、佛盛儒衰,韩愈以正统继承者自居,与佛教顽强对抗。韩愈辟佛的勇气和思路对后人(尤其是理学家)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不过,这一传承谱系是经不起推敲的。一是因为孔子对曾子的评价不高,二是因为典籍既无曾子讲“中庸”并传子思,也无曾子传子思其他思想的记载。所以,李翱虽认同曾子所言恰为性命之说,但却强调子思作《中庸》才是“得其祖之道”,否定了其师韩愈的“曾子传子思”之说。因此,为使这一传承谱系可信,必须解决上述两个问题,这一工作是由二程完成的。
从韩愈上述所说的“盖”字可知,他对“思孟”之间的传授用了肯定的语气,而在曾子和子思之间用的是“推测”的语气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子思与孟子之间的传授关系自西汉以来就有此说。如刘向《列女传》云:“(孟子)旦夕勤学不息,师事子思,遂成天下之名儒。”[40]后,东汉的班固、赵岐、应劭等人皆如是言。至于汉人有何依据而如此说,则不得而知。考之《孟子》,孟子从未说自己的老师是子思,只是说“予未得为孔子徒也,予私淑诸人也”,“乃所愿,则学孔子也”。[41]考之《荀子》,荀子虽有“子思唱之,孟轲和之”[42]之说,但也没有说子思亲授孟子,只是说在“五行”的观点上,两人的看法是一致的。可能因此,司马迁的说法比较圆融:“受业子思之门人,”至于太史公有何依据难以确定。[43]虽然班固与司马迁的说法不同,至少表明自汉以来,诸说皆认为子思、孟子是有关系的,且主张“亲授”的人很多,故而韩愈用了“肯定”的语气。但确言“曾子与子思”的传授关系,唐以前未见,虽孟子有“曾子、子思同道。曾子,师也,父兄也;子思,臣也,微也。曾子、子思易地则皆然”[44]之说,然并未说曾子是子思的老师。《孔丛子簚居卫》《礼记簚檀弓上》载有曾子与子思之对答,但从两人的语气看,明显不像是师生关系。《礼记》中子思批评曾子守丧之法过了,[45]据此可推曾子非是师,而可能相反。《孔丛子》则完全表明两人之对立的观点(一者尊君,一者则非),显然两人也非师生关系。[46]故而,韩愈用的是“推测”之语气。二程则不然,不仅肯定思、孟的亲授关系,而且把韩愈的说法做实。
要在曾子与子思之间建立“亲授”关系,从文献上寻求依据是行不通的,因为存世的文献都没有这样的说法。于是,二程另辟蹊径,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自圆其说。
其一、破除“十哲”之论,抬高曾子地位。《论语》有“四科十哲”之说,而曾子不在其中。对此,程颢认为“十哲”之说是世俗之论,所谓的“四科十哲”只是“乃从夫子于陈、蔡者尔”。曾子之所以没有跟随,乃是因为“曾子传道而不与焉”。[47]
其二、破除曾子“鲁”的标签。二程认为曾子始“鲁”而终“不鲁”:“曾子少孔子,始也鲁,观其后明道,岂鲁也哉?”[48]据《史记》,曾子少孔子46岁,孔子传之于孝道,而后作《孝经》。程颢于是据此推断:既然孔子都认为其“能通孝道”,[49]且得仲尼亲传,因此其“鲁”也只能是始学之初的情况,明道后肯定不会了。
接下来,二程重新诠释“鲁”之含义,使之由贬义变成褒义。孔子对曾子的评价是“参也鲁”。按照孔安国、邢昺的解释,“鲁”是“迟钝”[50]之意。不管这一解释是否符合孔子本意,可以确定的是,在这里的“鲁”明显是个贬义词,是与“愚”“辟”“喭”并列的。而二程却着力使之成为一个褒义词:“曾子传圣人道,只是一个诚笃。《语》曰:‘参也鲁。’如圣人之门,子游、子夏……卒传圣人之道者,乃质鲁之人。人只要一个诚实。圣人说忠信处甚多……曾之后有子思,便可见。”二程先从与同学的关系层面说,曾子实与可传圣人之道的子游、子夏一样皆是“质鲁”之人;后又从师生层面言,既然子思在曾子其后,如果说子思“鲁”,怎么可能成立呢?同时,二程把“鲁”之含义转变成了“诚笃”“诚实”,且与“忠信”紧密联系在一起。经过上述一番解构和论证,于是二程便顺理成章、理直气壮地认为“颜子默识,曾子笃信,得圣人之道者,二人也”,然“颜子没后,终得圣人之道者,曾子也”。[51]
其三、创造性诠释曾子所传“圣人之道”。二程说:“自曾子守义,皆说笃实自内正本之学”。曾子之学不仅是“孝道”,而成“内正本之学”了。那子思如何传曾子之学呢?二程以《中庸》为中心进行论证:“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,果可以一贯,若使他人言之,便未足信,或未尽忠恕之道,曾子言之,必是尽仍是。又于《中庸》特举此二义,言‘忠恕违道不远’,恐人不喻,故指而示之近,欲以喻人,又如禘尝之义,如视诸掌,《中庸》亦指而示之近,皆是恐人不喻,故特语之详。然则《中庸》之书,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,子思恐传授渐失,故著此一卷书。”[52]虽在《论语》中,孔曾之间确曾有“吾道一贯”的对话,但这并不能说明孔子只信曾子,因为《卫灵公》也载有孔子与子贡之间大体一致的谈话。所以二程“曾子言之,必是尽仍是”是武断之言,难以取信。二程为使之可信,找到的关键文献依据就在于《论语》《中庸》皆有“忠恕”之语。《论语》中,曾子以此语概括孔子“一以贯之”之学,《中庸》虽未显示与曾子有关,但此语既然是曾子所说,而在《中庸》中又出现过,于是二程就推断:如果不是曾子传给子思,为何会出现在《中庸》呢?二程经过如此论证,曾子就成为圣人之道的正统传人,于是曾子与子思之间的亲授关系(包括传授“中庸”思想)就建立起来了。再加上汉以来就有的思孟传授说法,孔、曾、思、孟的传承谱系便得以确立。
后来,朱熹对此谱系加以了进一步完善:一是创造性地提出了《大学》为曾子所撰,因而就有了“四子之书”的说法;二是对《中庸》前后文体不一(前半部分为语录体,后半部分为议论体)的特点作出了合理性的解释,于是有“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,更互演绎,作为此书”[53]之说。
总之,为了对抗佛统,二程、朱子在韩愈的基础上,建构并做实了上述儒家道统传承谱系,尽管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的良苦用心,尽管这也是宋学创新精神的反映,但他们的说法难免牵强附会,经不起文献的检验。
结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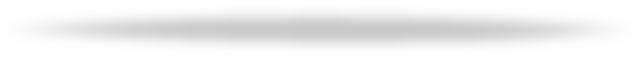
以伏羲为首、思孟学派为主,以“中庸”(或《中庸》)作为传承核心内容的儒家道统谱系的建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孔颖达率先以“中庸”为基点,统一了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。尔后,柳宗元以此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,并认为是圣人一脉相承的。宋初的孙复、胡瑗作了更进一步的推进和完善。紧接着,二程、朱熹在继承韩愈和柳宗元道统观的基础上,把孙复、胡瑗、契嵩等人的道统观综合在一起,并做了进一步的论证,最终使之确立与成型。
柳宗元、韩愈都是在梁肃和禅僧的影响下建构儒家道统的,且两人都以文见长,两人的道统观还各有特色与不足。前者在于以“中庸”为核心,但只是论及孔子;而后者虽以“仁义”为核心,却建构了孔、曾、思、孟的传承谱系。尽管如此,其中都有为理学家所借鉴与吸收的地方。然而,为何柳宗元的道统观在理学家中几无影响,而韩愈的影响很大呢?缘由在于两人对佛教的态度根本不同。韩愈是辟佛的巨匠,而柳是儒佛的调和者,甚至还以“大中”(即“中庸”)作为两家的共同点,如他在《南岳云峰和尚碑》中说:“师之教,尊严有耀,恭天子之诏,维大中以告,后学是效。”[54]“大中”本为儒家所固有,柳却认为佛教也讲“大中”,如此就把儒释会通起来。这一立场和做法定然会被大多数宋人,尤其理学家所批评。如朱熹就认为“柳子厚却反助释氏之说”,[55]后学黄震更是有“于圣人,凡皆不根于道故也”[56]之严厉批评。然而,今天的我们则可持一个客观的立场:尽管柳调和儒佛,但他以“中庸”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,并且认为这一思想是圣人一脉相承的,这不能不说是理学家道统观一个重要来源。遗憾的是,这一现象被学界长期忽视。
程朱所建构的儒家道统谱系,在当时就遭到了士人的质疑。如叶适不仅怀疑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传说的真实性,“《易传》虽有包羲、神农、黄帝在尧之前,而《书》不载,称‘若稽古帝尧’而已”,而且明确否定孔-曾-思-孟的传承谱系,“然则言孔子传曾子,曾子传子思,必有谬误”。[57]若从理学家的立场出发,我们可以发现,上述儒家道统的建构,与其说是历史的还原,不如说是学术的新诠。表面上看,其重要缘由之一是为统一儒家经典,如弥合《易传》以“伏羲、神农”为首与《尚书》以“尧舜”为首的不同说法,又如填平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之间的传承裂缝,然而,从朱熹“程夫子兄弟者出,得有所考,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”[58]之语,可明显看出,他直接跳过汉唐儒士,以二程接续孟子,即便加上《伊洛渊源录》《近思录》两书中的周敦颐、张载等宋儒,其所建构的道统谱系亦只是非连续的传承系统。故,上述儒家道统的建构目的不是历史的还原,而是理学立场的张目与儒家自信的重建。尽管朱熹建构的传承谱系与历史真实有很大的距离,但因其是足以与佛学媲美的宏大体系,加之随着程朱理学逐渐被朝廷重视,尤其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被奉为科举考试标准以后,理学家的道统观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并最为人所熟知。
注释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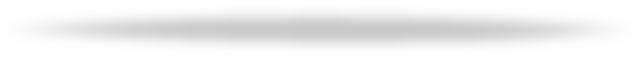
[1]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4-15页。
[2]朱熹在《大学章句序》中说:“大学之书,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……此(按:教人以复其性)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,所以继天立极,而司徒之职、典乐之官所由设也。” 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页。
[3]伏羲、神农、黄帝是如何被纳入儒家道统谱系的,可参见张培高:《伏羲、神农、黄帝纳入儒家道统谱系的由来、变迁及其原因》,《中国哲学史》2017年第2期。
[4]孔颖达:《礼记正义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1459页。
[5]孔颖达:《尚书正义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94页。
[6]段玉裁:《说文解字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20、116页。
[7]孔颖达:《尚书正义》,第376、551页。
[8]孔颖达:《周易正义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183页。
[9]学界对孔安国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,但按《汉书》记载看,以“大中”释“皇极”似已是当时较为普遍的做法。而且据孔光之说,之所以如此说,他也是据前人而来的。因此,孔安国极可能确有此论。《汉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4年,第3359、3443页。
[10]孔颖达:《尚书正义》,第307-308页。
[11]孔颖达:《周易正义》,第2-3页。
[12]《韩愈集》,长沙:岳麓书社,2000年,第408-409页。
[13]吕温:《吕衡州集》卷三《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2年,第1077册,第613页。
[14]《柳宗元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9年,第674页。
[15]参见尹邦志:《佛教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影响——以李翱〈复性书〉为例》,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2017年第4期。另柳宗元作有《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》,表明禅宗的法统此时已形成。
[16]《韩愈集》,第145页。
[17]与“中庸”含义相同的词(如“大中”“中”“中正”等)在柳文中相当常见。
[18]柳宗元:《柳宗元集》,第88、852、850、89页。
[19]章士钊:《柳文指要》上卷,北京:中华书局,1971年,第258页。
[20]就笔者所见,最集中探讨柳之“中庸”解说的文献见于张勇:《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》,合肥:黄山书社,2010年,第31-37页。但无论张勇所列的学者,如章士钊、孙昌武、陈弱水等,还是他本人,都未将柳宗元与理学关联起来。
[21]李翱:《李文公集》,郝润华校点,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与研究中心:《〈儒藏〉精华编202下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9年,第1339 页。
[22]《孙明复先生小集》,陈俊民校点,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与研究中心:《〈儒藏〉精华编205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4年,第33、34、29页。
[23]蔡方鹿曾论及孙复思想的一个方面。参见蔡方鹿:《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9年,第247-250页。
[24]孙复道统观影响了弟子石介,但石介与其师有重大不同。在石介看来,“始于伏羲氏,而成终于孔子” 之“道”的根本内容为“五常之道”,且是“大中至正”的,“吾圣人之道,大中至正,万世常行,不可易之道也”。按此,“大中”只是“五常之道”的一个属性而已。参见石介:《徂徕石先生文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4年,第79、221页。
[25]参见张培高、张爱萍:《胡瑗经学的核心思想》,《中州学刊》2021年第7期。
[26]胡瑗:《周易口义》,陈京伟点校,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与研究中心:《〈儒藏〉精华编3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9年,第17、160页。
[27]胡瑗:《洪范口义》卷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54册,第472、471页。
[28]卫湜:《礼记集说》,长春:吉林出版集团,2005年,第2557页。
[29]契嵩:《镡津文集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091册,第506、444、581、440、581、444、419页。
[30]契嵩:《镡津文集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091册,第498页。
[31]可参看张培高:《司马光〈中庸〉诠释的特色及其不足》,《现代哲学》2020年第6期。
[32]程颢、程颐:《二程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4年,第164、146页。
[33]程颢、程颐:《二程集》,第1032、411、94页。
[34]程颢、程颐:《二程集》,第367、606、1182页。
[35]程颢、程颐:《二程集》,第327页。
[36]卫湜:《礼记集说》,第2542页。
[37]吕大临:《礼记解》,陈俊民:《蓝田吕氏遗著辑较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3年,第270页。
[38]尹邦志:《佛教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影响——以李翱〈复性书〉为例》,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2017年第4期。
[39]《韩愈集》,第147、254页。
[40]张涛:《列女传译注》,济南:山东大学出版社,1990年,第38页。
[41]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295、234页。
[42]梁启雄:《荀子简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63页。
[43]《史记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3年,第2343页。不排除司马迁所言的可靠性。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虽有“善不(善,性也)。所善所不善,势也”之说,但又有“道四术,唯人道为可道也……爱类七,唯性爱为近仁。智类五,唯义道为近忠。恶类三,唯恶不仁为近义。所为道者四,唯人道为可道也”之论,显然已倾向性善论。《中庸》以“中和”“诚”论性,其“善性”的主张更为明显。依此,孟子后来主张性善论,完全可能受了子思门人的影响。参见李零:《郭店楚简校读记(增订本)》,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7年,第136-138页。
[44]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300页。
[45]曾子谓子思:“伋,吾执亲之丧也,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。”子思曰:“先王之制礼也,过之者俯而就之,不至焉者跂而及之。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,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,杖而后能起。”参见孔颖达:《礼记正义》,第200页。
[46]王钧林、周海生:《孔丛子译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9年,第94页。
[47]程颢、程颐:《二程集》,第385页。
[48]程颢、程颐:《二程集》,第385页。
[49]《史记》,第2205页。
[50]邢昺:《论语注疏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149页。
[51]程颢、程颐:《二程集》,第211、119、108页。
[52]程颢、程颐:《二程集》,第363、153页。
[53]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5页。
[54]《柳宗元集》,第164页。
[55]《朱子语类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2952-2953页。
[56]黄震:《黄氏日抄》卷六十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708册,第505页。
[57]叶适: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四十九,北京:中华书局,1977年,第735、739页。
[58]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5页。

